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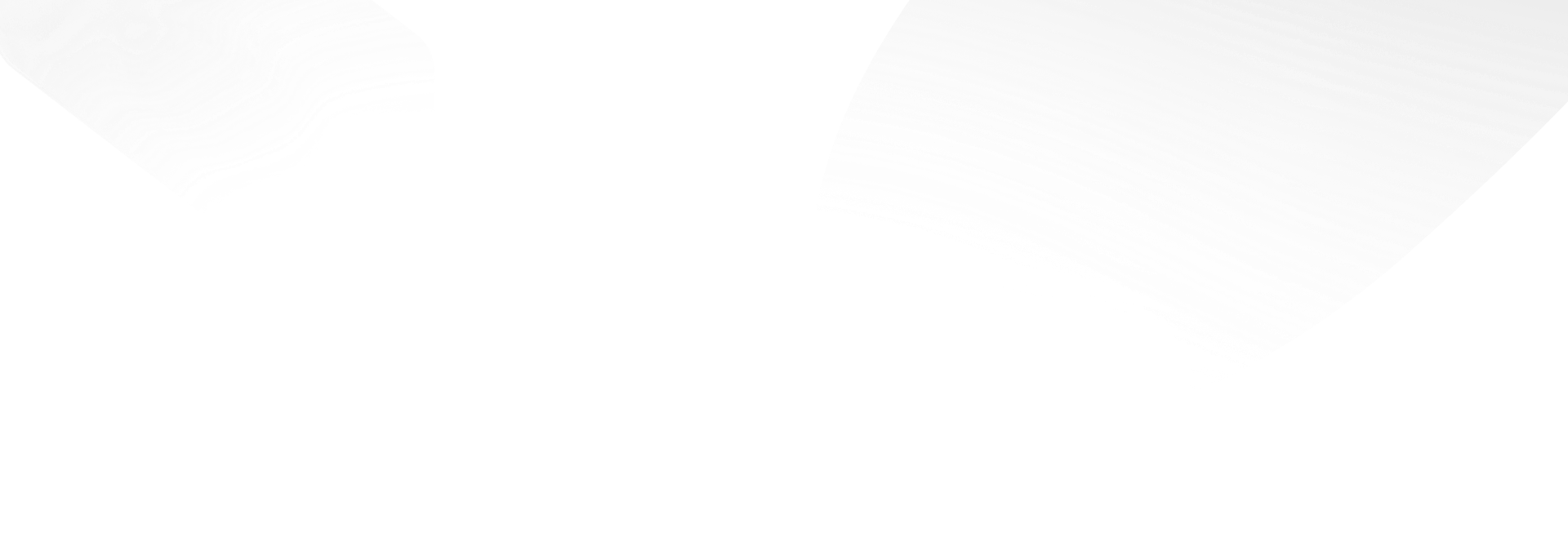
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法律关系刍议
——周晓钰胡忠惠 律师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生工伤,可以依照相关工伤保险法律规定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形下,劳动者也有权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主张民事侵权赔偿。如,劳动者患职业病,应当认定为工伤,可以要求社会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给予落实工伤保险待遇;而劳动者同时认为其患职业病的原因在于单位防护措施不力,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故又产生民事侵权赔偿的请求权问题。又如,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属于工伤,社会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应为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而事故伤害肇事方因其侵权行为也同时对劳动者负有赔偿责任。
工伤保险赔付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社会保险类法律,侵权损害赔偿依据侵权责任法之类民事法律,在法律关系上一为公法领域,一为私法领域,故两者存在诸多不同。略而言之:
一是目的宗旨不同。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1],旨在使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伤害或者罹患职业病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侵权损害赔偿其着眼在于填补损害,使受害人能够恢复损害发生前之原状,预防并制裁民事侵权行为。[2]
二是构成要件不同。劳动者的伤患被认定为工伤,即可依照程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或者其他第三方加害人是否存在过错,一般在所不问。侵权行为的成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以侵权人存在过错为必须。受害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
三是责任范围不同。工伤保险待遇仅及于人身损害相关之项目,包括医疗费、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辅助器具费、生活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损失补偿以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补助和停工留薪期等保障。而侵权损害赔偿以填补受害人损失为宗旨,故其赔偿范围除人身损害之外,还可以及于物的损害,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亦得产生精神损害赔偿。
四是主张权利程序不同。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需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必要时经过劳动能力鉴定,再由保险部门和用人单位落实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因工伤认定、经办机构核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等发生纠纷,则可社会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解决争议;如果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工伤待遇发生争执(特别是在用人单位未交工伤保险的情况下),则属于劳动争议,按照劳动争议的程序处理,要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然后才能进行司法审查。在仲裁和诉讼中,用人单位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对于某些事实要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而侵权损害赔偿则适用一般民事赔偿程序,如因赔偿发生纠纷,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在上述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工伤劳动者能否因一次工伤既主张落实工伤保险待遇又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对此,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十分清晰,司法实践中的处理也不尽一致,导致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
对于两种请求权竞合时的取舍问题,世界各国的态度不同,分别形成了四种模式[3]:
1.择一选择模式。即劳动者只能在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中选择其一。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曾经一度采用此种模式,但后来均已被废除。
2.替代模式(又称免除模式)。即劳动者只能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而不能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德国是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
3.兼得模式。即允许劳动者同时要求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所以又称相加模式、双重赔偿模式。采取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
4.补充模式。即允许劳动者同时要求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但最终所获赔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此种模式下,因为劳动者在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其中一个程序中获得赔偿后只能在另一程序中就差额部分获得赔偿,所以又称补差模式、差额模式。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有日本、智利及北欧等国。
上述模式,基本上涵盖了处理此问题的各种可能方案,并各有其适用理由。笔者认为应当遵从保障工伤劳动者生存利益,维护法律体系的公平、统一之原则,并结合工伤保险制度及侵权责任法制度的现有规定,综合衡量确定适宜的模式。
二、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现状
对于如何处理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的竞合关系,目前我国法律虽有所涉及,但规定并不明确和统一,各地审判实践亦处理不一。
立法方面,1996 年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明确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采用交通事故侵权赔偿优先、工伤保险补充的原则;并且不允许受害人获得侵权和工伤的双重赔偿,但可以获得差额补偿。[4]但交通事故以外的工伤如何处理,则不甚清楚。2003 年国务院制定的《工伤保险条例》取代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但《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赔偿与侵权赔偿竞合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在制定实施意见时,大多采用差额模式。[5]
《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有论者认为是兼得模式[6],也有论者认为是补充模式。[7]而2006年6月1日起施行的《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41条规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死亡的,死亡者家属除依法获得工伤保险补偿外,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还应当向其一次性支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赔偿金。”明确了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工亡的劳动者家属可获得双重赔偿。
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 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解释》明确了侵权责任人是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劳动者只能选择工伤保险赔偿,此种情况为替代模式;对于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是采取兼得模式还是补充模式,没有作出明确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 号)中指出,“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这其实是明确采用了兼得的救济方式。
2010颁布的《社会保险法》第42 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从规定来看,劳动者就医疗费用不能获得双重赔偿,因为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医疗费用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即第三人应向工伤保险基金赔付,劳动者自然无法从第三人处再获赔偿。然而,该条规定仅涉及工伤医疗费用,至于工伤医疗费用之外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如伤残补助金( 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等,劳动者是否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立法却语焉不详。许多论者认为该法既然未规定医疗费以外项目的追偿,则可认为是支持医疗费以外项目的双重赔偿模式[8]。但2011 年实施的《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个人已经从第三人或者用人单位处获得医疗费用、工伤医疗费用或者工伤保险待遇的,应当主动将先行支付金额中应当由第三人承担的部分或者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退还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或者工伤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向第三人或者用人单位追偿。”该规定又采用了补充模式。但该办法作为行政规章层次较低,其是否有权对法律作出扩大解释则存在问题。
在司法实践方面,由于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及处理规则,导致司法实践操作不一致。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域的法院对工伤保险待遇与侵权损害赔偿竞合所作的判决也不尽一致。既存在补充模式[9],也存在工伤赔偿取代模式[10],更存在兼得模式[11]。在兼得模式中,既有完全双重赔偿的[12],也有扣除医疗费等实际发生费用后支持双重赔偿的[13],还有本身就是用人单位既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任又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14]。
三、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法律关系模式选择之建议
选择模式允许劳动者在两种请求权中择一而行,一经选定则不能变更,该模式虽然符合请求权竞合时的通常法律处理原则,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对劳动者颇为不利。工伤事故发生之初,面对工伤赔付程序之复杂、民事侵权索赔举证之困难、两种赔偿数额比较之不确定性、诉讼风险及执行风险之难测,即使专业律师也很难准确判断选择何种程序为最优。对于处于弱势地位之劳动者,选择难度则为之更甚。所以这种模式显然并不利于劳动者权益保护,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一度采取此方式,后又抛弃,可见不值借鉴。
替代模式将工伤保险赔付作为劳动者获得救济的唯一途径,将侵权赔偿排除在外,主要考虑工伤保险制度由国家公权力部门执行,劳动者一般较易获得保障,且可以减少诉讼,避免争议,有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但此制度驳夺了劳动者民事侵权赔偿的请求权,本身其合理性就乏依据,尤其工伤保险不支持非人身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很多情况下使劳动者所获赔偿较之侵权赔偿数额为低。如没有完善追偿制度或者社会保险部门怠于行使追偿权,还使民事侵权人免于被追责,从而使侵权责任法预防和制裁民事侵权行为的目的落空。故替代模式也不可取。
兼得模式最有利于劳动者,目前对现行立法的理解及司法实践的倾向多采此说。但笔者认为依此模式并不妥当,相比较而言,补充模式最为合理可行。理由如下:
1.无论是按照工伤保险制度赔付,还是依照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赔偿,劳动者所受的损害基本都可得到填补,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在任何一种赔偿制度中也都可基本得到解决,尤其《工伤保险条例》经过修改,相关赔偿项目与民事侵权赔偿项目更加趋同,[15]双重赔偿与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目的,有所背离。支持双重赔偿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工伤保险赔付数额相对较低,不足以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但这一缺陷如果存在,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解决,而无需通过双重赔偿。实际上,《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工伤待遇标准已经通过修改调高。
2.允许工伤劳动者获得双重赔偿,可能使劳动者得到超出其损失之利益,对于因其它侵权受到伤害的权利人而言,很不公平,从而撕裂了侵权责任法的公平体系。当民事侵权责任人也是用人单位时,用人单位除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外,还要承担工伤保险金支付责任,在未履行保险金支付义务的情况下还须承担双份赔偿,这对用人单位也属不公。大概也是考虑到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负担过重,显失公平,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权责任人是用人单位时采用替代模式,即只允许劳动者主张工伤保险赔偿。此规定下仅因侵权责任人不同,就使劳动者在遭遇性质相同的两种侵权时,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于侵权责任人是用人单位时的受害劳动者殊为不公。
3.允许劳动者获得双重赔偿,因较之单一赔偿利益相差悬殊,易引发道德风险。相关利益方为工伤是否构成、侵权责任是否成立无不极力相争,为此增加讼累,产生违规乃至违法做假等事件也在所难免。
4.社会保险资源宝贵,在我国更存在社保资金缺口过大的困难,双重赔偿无疑在为工伤劳动者“锦上添花”的同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所以,在劳动者因工伤产生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请求权竞合时,应当允许劳动者同时要求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但最终所获赔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这其中两种赔偿程序中应予抵消者,不仅包括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可补偿性损失发生费用[16],也应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不可补偿性损失所产生费用。因为工伤保险待遇之中的工亡补助金、伤残补助金与民事侵权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具有同质性。
四、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以补充模式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司法审判标准,这是笔者针对本文论题的基本观点。在实际操作中,尚有以下问题需要明确:
1.程序问题。
(1)对于劳动者或其亲属主张工伤保险给付或民事侵权赔偿不宜设定先后顺序限制。即应允许其先提出任何一种请求,也应允许其同时提出两种请求。以此充分保障、维护劳动者及其亲属的请求权。
(2)劳动者或其亲属已经主张工伤保险给付,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无论该侵权人是用人单位还是第三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劳动者及其亲属已经申请仲裁或起诉法院要求用人单位落实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或要求用人单位因未缴纳工伤保险费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又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赔偿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无论该侵权人是用人单位还是第三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抵消问题
(1)劳动者及其亲属已经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赔偿,又在侵权民事诉讼中要求用人单位或第三人承担相同或同类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如果相同或同类赔偿项目,根据法律在民事侵权赔偿诉讼中数额较高的,超出工伤保险给付部分的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劳动者及其亲属已经通过工伤保险获得相应赔偿,又在侵权民事诉讼中要求用人单位或第三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等与工伤保险给付不相同且不同类赔偿的,经审查符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劳动者及其亲属已经通过民事侵权赔偿程序获得相应赔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在落实相关工伤保险待遇时,可以扣除其已经获得赔偿的相同或同类项目金额。如果相同或同类赔偿项目工伤保险数额较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应将差额支付劳动者或其亲属。但停工留薪期待遇、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伤保险特有项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用人单位不得扣除。
3.追偿问题
(1)社会保险机构在承担工伤保险给付之后,可以就其给付范围内的项目向侵权行为人追偿,该范围不仅指《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医疗费,还应包括交通费、护理费等可补偿性损失发生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不可补偿性损失所产生费用。
(2)追偿对象一般为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也可以是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工伤事故伤害的用人单位。换言之,除非用人单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伤劳动者,一般情形下,社会保险机构不得向用人单位追偿,这是因为工伤保险实际也涵盖了责任保险的性质,具备分散、转移用人单位风险的功能。
(3)用人单位因未缴纳工伤保险而向劳动者或其亲属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可以向负有侵权责任的第三人进行追偿。 因为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所承担的责任是违法不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律后果,而非对工伤劳动者负有直接伤害责任。
(4)劳动者及其亲属虽经法院审判获得侵权赔偿胜诉判决,但未获执行的,社会保险机构及用人单位应为其落实工伤保险待遇且不得主张抵消判决书相关赔偿项目。社会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后,可依法获得追偿权。必要时可取代劳动者及其亲属成为执行申请人,或者与劳动者及其亲属共同成为执行申请人。
4、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问题。
(1)工伤保险赔付适用无过错原则,只要劳动所受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或出现职业病伤害,社会保险机构及用人单位就应为其落实工伤保险待遇,而不论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而在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中,则存在《侵权责任法》第26条所规定的,过失相抵问题。但通常认为,如果侵权责任人为用人单位(雇主),除非是劳动者(雇员)重大过失所造成损害,一般不宜适用过失相抵。
(2)对于侵权赔偿关系中适用过失相抵时,对于劳动者所主张的差额补偿,则应根据实际赔偿比例进行换算抵顶,不能以赔偿总额简单抵顶。如某一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受伤,同时符合工伤条件,工伤保险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万元,而在侵权赔偿诉讼中,认定当事双方各负有50%过错责任,残疾赔偿金总额为5万元,而侵害人应赔偿该受害劳动者数额为2.5万元。以总额算,似乎该劳动者不能从侵权人处获得补差。其实不然,因侵权的残疾赔偿金总额为5万元,高出工伤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万元,过错程度为各负50%,则该劳动者有权要求侵权人赔偿其差额1万元,侵权人另外应当赔偿的1.5万元,由社会保险机构获得追偿权。
[1]《工伤保险条例》第1条。
[2]《侵权责任法》第1条。
[3]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11页。
[4]《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 条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该办法同时规定,“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5]《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44条规定,“因机动车事故或者其他第三方民事侵权引起工伤,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基金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先期支付的,工伤人员或者其直系亲属在获得机动车事故等民事赔偿后,应当予以相应偿还。”《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实施细则》第33 条规定,“同一工伤事故兼有民事赔偿和商业性人身、人寿保险赔偿的,被保险人因未能及时获得民事赔偿和商业性人身、人寿保险赔偿而危及生命或对其康复有严重影响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垫付工伤医疗费用,以保证被保险人得到及时抢救、治疗。在被保险人获得民事赔偿和商业性人身、人寿保险赔偿时,应偿还工伤保险基金垫付的费用。”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意见》第10条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机动车事故伤害……按《条例》规定认定为工伤和视同工伤的……如第三方责任赔偿低于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因其他原因使工伤职工未获得赔偿的,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规定补足工伤保险相关待遇。”《苏州市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同一工伤事故兼有民事赔偿的,按照先民事赔偿、后工伤保险支付待遇的顺序处理。民事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工伤保险不重复支付相应待遇,民事赔偿支付的上述待遇标准低于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补助足差额部分。”
[6]袁合川:《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救济模式》,《中国劳动》2013年4期,第18页。
[7]周立:《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法律关系分析与裁判路径选择》,《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2辑(总第46辑),第55-56页。
[8]袁合川《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救济模式》,《中国劳动》,2013年第4期, 19页。
[9]广东省江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之(2006)湛中法民事终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认可一审法院“依法享有请求运输公司赔偿的权利,将工伤待遇和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相互竞合,实行差额互补”的观点,认为一审原告所主张的残疾补助金,应扣除“已经从运输公司领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偿金”。参见《人民司法》2006年第6期,第70-73页。
[10]笔者代理的某职工诉用人单位劳动保护不力致人身损害赔偿案,法院告知按工伤认定程序办理而不予受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8期所载杨文伟与上海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法院认定“杨文伟作为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宝二十冶公司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因此而有所加重。”
[12]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诉郑某人身损害赔偿案中法院认为,“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以原告张某享有主张双重赔偿的权利。”该判决全面支持双重赔偿。参见《当代广西》2010年8月第15期,第50页。
[13]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法院审理的吴月凤与某电器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法院认为,“吴月凤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先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并无法律规定不可再向用人单位要求工伤保险赔偿,但再请求用人单位赔偿工伤保险待遇时,用人单位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中应扣除第三人已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辅助器具等实际发生费用。本案被告吴月凤现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在与侵权不同的赔偿范围内要求赔偿并非双重赔偿。”参见《劳动保护》2011年第1期,第71页。
[14]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一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许士明、宗秀珍诉孙望、李翠夫妇以及某铁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之子在某铁矿工作期间被案发时无行为能力的工友用刀杀死,在落实工伤待遇之后,原告将作案人的监护人及某铁矿诉诸法院,再要求侵权赔偿。一审法院判定被告孙望、李翠夫妇以及铁矿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4 万余元,其中孙望、李翠夫妇承担30%的赔偿责任,铁矿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铁矿不服,提起上诉。二审调解达成协议,原告获得31万元赔偿。参见孟明智:《一场打了十六年的官司—全国首例用人单位承担职工“工伤、人身损害”双重赔偿的案件》,《学习月刊》2009年第4期上半月,52-54页。
[15]如
[16]“如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后续治疗费、丧葬费等,这些费用有具体的物质载体体现,依据支出或相关票据可以计算出来,是受害方实际支出的费用,故称之为可补偿性损失;另一类是基于不可补偿性损失产生的费用,费用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死亡赔偿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等,这几项是针对人基本权利损害的赔偿,这些人身利益是不可恢复不可估量的损失,故称之为不可补偿性损失。”参见周立:《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法律关系分析与裁判路径选择》,《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1年第2辑(总第46辑),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