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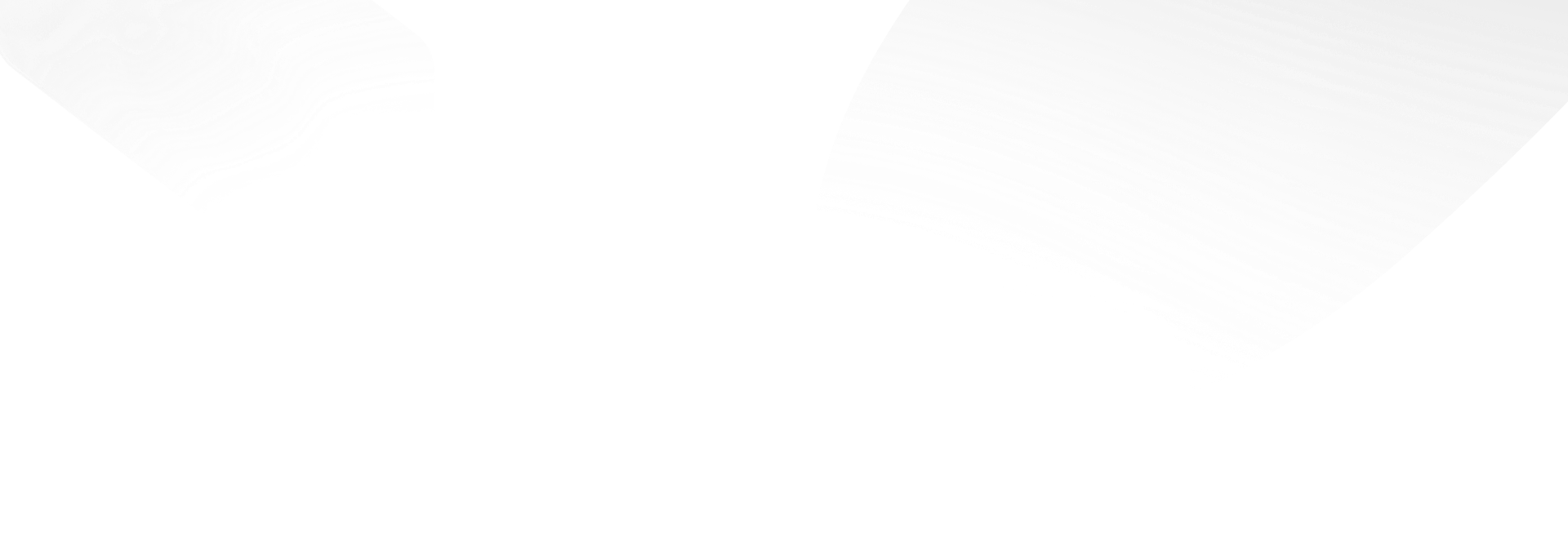
浅议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评判标准及举证责任
――王颖 律师
【基本案情】
1988年9月,宋某购买了王某私有平房三间,并支付购房款15500元,但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宋某将户口迁入该房屋后只是断断续续在内居住。2011年2月,王某去世,其女儿继承了王某已经卖出的房产,通过继承公证将房屋办至自己名下。同年9月,王某之女将面临拆迁的房屋又卖与赵某,在赵某支付了合理对价后双方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宋某知晓这一事实,将王某之女及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之女与赵某之间的转让行为无效。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对王某之女及赵某之间的房屋交易细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在问到双方在交易时是否到过诉争房产实际查看房屋时,两被告均称没有,法官遂以该交易细节不符合日常房屋交易习惯,系恶意串通,判决两被告房屋转让行为无效,赵某不构成善意取得。该案例中,赵某受让诉争房屋是否善意是本案双方争执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在规定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时,仅在第1款中指出“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却并未界定“善意”的概念和标准。然而,善意又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整个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所在。
【善意的涵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再结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善意取得成立要件的规定,可将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界定为:第三人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事项的信赖,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并且转让的不动产已经登记于该第三人名下。此时,若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与真正权利人不符,善意第三人也即时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而不受真正权利人追夺,真正权利人只能请求登记记载的权利人或有过错的登记机关赔偿。这是一种牺牲财产静的安全保障市场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但这样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即第三人对于不动产登记簿所载事项的信赖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原因,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第三人在受让时是否真的不清楚也不应当清楚不动产的真正权利归属。这个心理过程是极具主观色彩的,需要法官根据交易细节加以推断。
考虑到善意取得制度在于兼顾所有人之利益与交易安全,使第三人承担一定程度的注意义务本无可厚非。但司法审判亦应坚持主客观结合的标准进行判断,不能对第三人过于苛刻,不能因为第三人有一些轻微过失就视其为恶意。故只要第三人没有故意和重大过失,就应认定其为善意。上述案例中,主审法官认为王某之女与赵某之间没有详细的实地了解诉争房产,不符合房产交易双方的正常心理和行为,赵某所称的“善意”不能令人信服,对于这样的主观评判是否合理,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尽管大部分人在交易房产时,是要对房屋“验明正身”的,但这并非是一道必经程序,本案中赵某恰恰所需要的就是一套即将拆迁的房屋,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是完全没必要去看一套破落的平房院落,她只需要保证自己能够顺利取得拆迁房产的替代利益就行了。
【善意的举证责任分配】
第三人主观上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还必须通过证据加以查明,这就涉及到善意的举证问题。那么,到底是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为善意?还是由真正权利人证明第三人非善意?举证责任的承担规则不同,往往影响到裁判结局,尽管其本身并不直接关乎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关于“善意”的证明责任分配,有两种观点: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善意取得诉讼案件中,真实权利人通常都是处于原告的地位,那么他就有义务证明第三人为恶意,第三人举证证明其为善意作为抗辩的理由。二、应当由第三人证明其受让时是善意的负举证责任。因为如果要求真实权利人就其主张的非善意事实举证,其败诉的风险将加大,明显增加了追
回标的物的难度,这与我国《物权法》精神向冲突,在法律上也没有根据。而且如果当一方当事人举证困难,而另一方当事人从反面举证相对较为容易时,可以考虑在不违背实体法立法目标的前提下,让举证较为容易的当事人从事实的反面承担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能够满足人们对实体正义的追求。
笔者倾向与第一种观点。判断善意取得是否成立本身就是对真实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的一种取舍。况且举证责任倒置是对“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基本原则的突破,是针对举证责任双方力量严重失衡时的一种权宜之计。既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就不应当被经常采用。而且笔者认为,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应当由法律来规定,而不宜由法官视具体情形随意变通,这极易导致审判权利的滥用。
当然由真是权利人承担举证责任确实存在一定弊端的:因为对于转让过程中出让人和第三人的心态,第三人是最清楚的。真实权利人离交易的事实和证据相当遥远,将很难收集证据来证明第三人的行为系恶意行为,这就很可能使得原本为维护交易秩序目的所设计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标落空,最终导致大量的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合谋的行为。但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本身就不是为了单纯保护某一单方权利人的利益,而是在二者利益相冲突时作出的一种权衡和取舍。况且法律亦考虑到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救济途径,他可以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来弥补因此而遭受的损失。